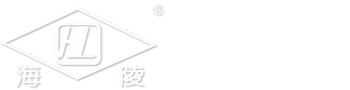應摒棄“私募股權眾籌融資”的概念,與證券法修改同步,依據“小額發行豁免”的思路,由中國證監會制定相應的權益類眾籌規則法治周末特約撰稿
邢會強
日前,中國證券業協會公布了專門針對私募股權眾籌平臺的自律管理規則—《私募股權眾籌融資管理辦法(試行)(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
《征求意見稿》將股權眾籌融資定性為非公開發行性質,并創造了“私募股權眾籌”的概念。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指出,以是否采取公開發行方式為劃分標準,股權眾籌分為面向合格投資者的私募(非公開發行方式)股權眾籌和面向普通大眾投資者的公募(公開發行方式)股權眾籌。
目前,中國證監會正在抓緊制定股權眾籌融資的相關監管規則,以公開發行方式開展股權眾籌融資的相關政策也正在研究中。
筆者認為,“私募股權眾籌”概念的邏輯是自相矛盾的,這一提法不能成立,更不能進入法律規制的視野。應摒棄“私募股權眾籌”的概念,不要將“私募”與“眾籌”相混淆,不必要出臺所謂的“私募股權眾籌融資管理辦法”,應回歸眾籌的大眾融資、小額集資,“屌絲金融”的本質,與證券法的修改同步。中國證監會盡早出臺相應的眾籌規則。g>眾籌興起的關鍵在于互聯網“眾籌”譯自英文“Crowdfunding”。2006年8月,美國學者邁克爾·薩利文第一次使用了Crowdfunding一詞。他將其定義為:Crowdfunding描述的是群體性的合作,人們通過互聯網匯集資金,以支持由他人或組織發起的項目。
2010年2月,《麥克米倫詞典》網頁版收錄了Crowdfunding一詞,定義為:“使用網頁或其他在線工具獲得一群人對某個特定項目的支持。”2011年11月,Crowdfunding作為新型金融術語被收錄于《牛津詞典》,即“通過互聯網向眾人籌集小額資金為某個項目或企業融資的做法。”
“Crowdfunding”起初介紹進入中國時,譯法并不統一,有的直譯為“大眾集資”,有的意譯為“公眾小額集資”。在2011年2月號的《創業邦》雜志《眾籌的力量》一文中,寒雨首次將Crowdfunding一詞譯為“眾籌”。這一譯法遂在中國大陸得到廣泛認可和流行。
目前,國際上對“眾籌”(Crowdfunding)的定義公認為:它是指通常通過互聯網平臺向一大批支持者(即“公眾”)募集資金以支持某一項項目的活動。
眾籌活動通常涉及三方面的當事人:發起人或發行人,即需要資金、發起項目,以獲得資金的個人或組織;公眾或支持者,即支持這一項目并提供資金的不特定社會群體,通常是收入相對較低的“網民”;眾籌平臺,通常是一個網站,通過這個網站,發起人和公眾撮合在了一起(當然也有少量線下眾籌撮合平臺)。
總之,國際上,眾籌主要是公開發行眾籌,眾籌主要依托互聯網。
也正是在互聯網時代,才使大規模的小額集資從過去的不可能在現在成為可能。因為互聯網使得信息傳播的范圍得以無限擴大,使信息傳播的成本得以極大降低。再加之網上支付功能、第三方平臺的興起和強大,終于催生了今天眾籌在全球的火爆局面。
如果全體中國人每人給你1元錢,你就會成為億萬富翁。這個邏輯大家都懂。在過去,這是萬萬不可行的,因為告知全體中國人你要1元錢的信息的成本極大,遠遠超過了13億元,你不可能成為億萬富翁,只能成為億萬“負翁”。再者,每一個人給你匯款的成本(包括時間成本和郵費)也較大,也遠遠超過了13億元,因此,給你1元錢大家都不在乎,但大家在乎的是給你匯款的麻煩和郵費。
但是,在今天,即使全體中國人每人給你1元錢還不可能,但上千萬網民每人給你一到一百元不等,使你成為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卻完全是有可能的。因為,通過微信的傳播,告知上千萬人甚至上億人你要一元錢的信息的成本很低,大家通過支付寶等網上支付工具給你1元錢的成本也很低。這就是眾籌得以可能,得以流行的邏輯。
在國外,股權眾籌主要是為初創企業提供資金。起初,為創業企業提供資金主要是天使投資人的事兒,或者說是風險投資(VC)、私募股權基金(PE)的事兒。廣大的網民由于資金不多,是玩不起VC、PE的。
但是,互聯網和第三方支付技術的出現使得廣大網民們有了玩VC、PE的機會,每個人為其看好的項目少投一點,成為“股東”,夢想著其投資的企業中,有一家會成為“微軟”、“Facebook”或“阿里巴巴”,對于“投資人”來講,即使投資都不成功,最終顆粒無收也無所謂,權當買彩票了(前提是投資額度占其收入或資產的比例不大),但萬一實現了呢?
而對于那些籌資人來講,則輕松解決了初創企業的首輪融資問題。上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對于一個創業者很重要。須知,馬云、馬化騰、丁磊當初都是50萬元人民幣起家的,李彥宏的運氣好些,第一輪獲得的風險投資是50萬美元。如果我是馬云的創始合伙人,即使比例很低,不斷被后輪融資所稀釋,我今天也不會覺得北京的房價高得難以接受了。
總之,眾籌興起的關鍵在于互聯網,眾籌火爆的關鍵在于“小額、分散”,聚少成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g>法律限制促“中國式眾籌”興起但是,眾籌引入國內時,在股權眾籌領域,由于法律限制,沒有人敢向超過200人以上的人來集資,否則就是“非法集資”,要受到法律制裁。再加上微信在華人圈的興起和流行,國人創造出了另一個模式的“眾籌”,或者說“中國式眾籌”。
“中國式眾籌”的特點在于,一是人數不能超過200人,二是在熟人圈中做股權眾籌。畢竟中國的信用體系未建立,熟人圈中做股權眾籌更容易成功,更適合中國的社會土壤。微信和支付寶使得在熟人圈中做股權眾籌很便利,這就是“中國式眾籌”得以成立、成功和流行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國證監會提出“私募股權眾籌融資”概念的理據所在。
但此“眾籌”已經非彼“眾籌”了。彼“眾籌”即Crowdfunding,是向大眾集資,集資是首要且唯一的目的。此“眾籌”即“中國式眾籌”,籌的不僅僅是錢,更是“合伙人”,是各“合伙人”的資源。“眾籌”成了“向大家要”,要錢、要人、要各種資源。
2014年12月25日下午,北京,在國家會議中心,“千人眾籌大會”召開。現場極為火爆,報名者高達兩千多人,最后篩選通過了一千多人,結果現場出席者高達1500多人。
會議需要舞蹈,籌備組在微信圈中信息一發,很快就有人報名,于是一場舞蹈有了,這就是“眾籌”。會議需要電子屏,籌備組在微信圈中信息一發,很快湊夠了3萬元,于是一幅巨大的電子屏有了,這也是“眾籌”。會議需要服務生,籌備組在微信圈中信息一發,很快就有二十多名志愿者報名,這還是“眾籌”。會議需要付會場租金,籌備組給參會者一發短信,結果700多人認捐了10多萬元,這仍是“眾籌”。盡管這都不是股權眾籌,但的確是“中國式眾籌”。
總之,“眾籌”在中國已經演變成了,或者更準確一點,是“通過微信向大家要”。
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中國式股權眾籌”只能是向特定對象進行的,股東人數不能突破200人的“私募眾籌”。只有“預售式眾籌”、“捐贈式眾籌”才可以公開發售,人數才可以突破200人。
合法的“私募股權眾籌融資”只能通過實體場所—如咖啡館,或者微信進行,沒有人敢通過互聯網網站進行,因為網站的開放性決定了這是在“向不特定公眾發行證券”,按照證券法,即使最終股東人數不超過200人,也是“非法發行證券”。
換言之,合法的“私募股權眾籌融資”其實是沒有眾籌網站平臺的,只有非法的、打擦邊球的股權眾籌才有眾籌網站平臺。當然,“預售式眾籌”、“捐贈式眾籌”大都有眾籌網站平臺,而這則是合法的。g>應摒棄“私募股權眾籌融資”概念合法的“私募股權眾籌融資”沒有眾籌網站平臺,非法的“私募股權眾籌融資”有眾籌網站平臺卻不合法。
但《征求意見稿》第二條“適用范圍”規定:“本辦法所稱私募股權眾籌融資是指融資者通過股權眾籌融資互聯網平臺(以下簡稱股權眾籌平臺)以非公開發行方式進行的股權融資活動。”這著實令人費解—通過互聯網平臺還能以非公開發行方式進行的股權融資活動?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征求意見稿》第十二條“發行方式及范圍”又從反面進行了解釋:“融資者不得公開或采用變相公開方式發行證券,不得向不特定對象發行證券。融資完成后,融資者或融資者發起設立的融資企業的股東人數累計不得超過200人。法律法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解析第十二條的規定可知,該條首先是從方式或過程的角度進行界定:“融資者不得公開或采用變相公開方式發行證券,不得向不特定對象發行證券。”這與互聯網網絡的開放性相沖突。
《征求意見稿》第五條“平臺定義”規定,股權眾籌平臺是指通過互聯網平臺(互聯網網站或其他類似電子媒介)為股權眾籌投融資雙方提供信息發布、需求對接、協助資金劃轉等相關服務的中介機構。
我們知道,在股權眾籌平臺上,符合條件的人均可注冊,成為融資者或投資者。哪怕是股權眾籌平臺實行會員制也是如此。這一開放性決定了,在股權眾籌平臺上發布融資信息,就已經是公開的方式發行證券,就已經是“向不特定對象發行證券”了。
這即是說,只要利用了股權眾籌平臺,就注定了是公開發行。
《起草說明》還說:“股權眾籌平臺只能向實名注冊用戶推薦項目信息,股權眾籌平臺和融資者均不得進行公開宣傳、推介或勸誘。”筆者覺得,難道股權眾籌平臺只能通過電子郵件推送推介書嗎?難道要禁止股權眾籌平臺在網頁上公開推介、展示嗎?
此外,現行《證券法》第十條規定:“公開發行證券,必須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條件,并依法報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或者國務院授權的部門核準;未經依法核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公開發行證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公開發行:(一)向不特定對象發行證券的;(二)向特定對象發行證券累計超過二百人的;(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發行行為。非公開發行證券,不得采用廣告、公開勸誘和變相公開方式。”
顯然,在互聯網上將眾籌項目予以公開展示,就屬于公開勸誘了,就屬于“向不特定對象發行證券”了,就屬于公開發行了。股權眾籌怎么還能通過互聯網進行私募?
前面所介紹的“中國式股權眾籌”,其實是通過微信等手段在熟人圈中進行的私募,盡管有些人稱其為“眾籌”,但已經不是法律意義上、需要法律進行規制的眾籌了。
筆者認為,“私募股權眾籌融資”,不應該進入法律的視野內,不應該進入法律規制的軌道上。像《征求意見稿》這樣樹立投資者適當性管理門檻,對眾籌平臺提出各種要求,進行各種備案和行為規制,這些條文、規則其實是無“用武之地”的。如果非要它有“用武之地”,則除了徒增“中國式股權眾籌”的成本之外,其實并無多大社會收益。
筆者認為,應摒棄“私募股權眾籌融資”的概念,與證券法修改同步,依據“小額發行豁免”的思路,由中國證監會制定相應的權益類眾籌規則。“小額發行豁免”即不超過一定額度的公開發行(比如300萬元),無論投資者人數多寡,均豁免向證監會注冊。
或許,有人擔心,眾籌以公開發行形式進行,無風險識別能力的“屌絲們”參與眾籌,會給經濟詐騙分子以可乘之機,從而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這一擔心不無道理,但也不是毫無辦法。
應對思路應該為:首先限制收入較低、資產較少的投資者的參與比例或數額;其次,對眾籌平臺實施執照管理、審批管理,而不是目前的備案管理(當然,要實施審批管理必須制定相應法律)。在此基礎上,主要依靠眾籌平臺的自律監管來驅逐失信者和違法者,這類似于打車軟件對違約者的懲罰。當然,這離不開證券市場誠信數據庫制度的支撐,失信的和違法的融資人及其實際控制人、控股股東和管理層的誠信記錄都要進入該數據庫,眾籌平臺和投資者應能查詢到該誠信信息;再次是完善投資者訴訟制度,為投資者起訴追討損失打開方便之門;最后則是公權執法的保障。由于眾籌都是實名管理,因此,公權機關對于違法犯罪行為的查處和處罰也比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