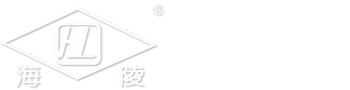虛假陳述案中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的協調銜接
張子學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北京100088)
摘要:基于最新的法院民事裁判與證監會的執法動向,本文圍繞虛假陳述案中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的協調一致與銜接互補,分析了民事司法與證監會的行政認定不一致、民事司法對證監會行政執法的反向推動與證監會行政執法對民事賠償的直接介入等三個問題,并建議借鑒參考SEC采用的“公平基金”制度、英國金融行為局近年開始使用的“直接勒令賠償”制度以及香港證監會推行的申請法院“責令回購”制度。
關鍵詞:民事司法;證監會執法;行政執法;協調銜接;虛假陳述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test trend of court civil judgement and CSRC enforcement act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coordination and convergence issues between civil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in misrepresentation cases, which are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civil judicature and administrative cognizance, the reverse promotion of civil justice to the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of CSRC, and the direct intervention of CSRC enforcement in civil compensation. The paper suggests using “The Federal Account for Investor Restitution FAIR Fund” adopted by the SEC, the “Order Compensation System” that the UK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has used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Repurchase of shares ordered by Court” implemented by the Hong Kong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Keywords:civiljustice,CRSCenforcement,coordination,convergence,misrepresentationcase作者簡介:張子學,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研究方向:金融監管、證券法、公司法。
中圖分類號:DF438 文獻標識碼:A
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以行政執法為主干、以刑事追究為后盾、以民事賠償訴訟(私人執法)為補充的三位一體、有機銜接、前后呼應、相互借助的證券執法機制。證監會對違法行為的線索發現與行政調查、行政處罰是證券執法的基礎和主干,公安、檢察機關不斷加大對內幕交易、操縱市場、“老鼠倉”、欺詐發行與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為的追究力度,法院受理與判決的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件也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證券執法的“力”、“量”比肩美國,在國際上獨樹一幟。同時,行政執法與刑事追究、行政執法與民事司法之間,也逐步暴露出一些需要引起注意、有待釋解的機制結點。在當前各方面形成合力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的整體背景下,本文基于最新的法院民事裁判與證監會的監管執法動向,圍繞虛假陳述案中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的協調一致與銜接互補,分析了民事司法與證監會的行政認定不一致、民事司法對證監會行政執法的反向推動與證監會行政執法對民事賠償的直接介入等三個相對獨立又有共性關聯的問題,提出了完善有關立法、司法與監管的建議,以期對進一步優化我國證券執法機制,更好發揮證券執法懲罰、警示與補償的三維功能價值有所裨益。
民事司法與證監會的行政認定不一致
近期,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北大醫藥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2018)渝01民初291號”判決書中關于信息“重大性”的意見,引起了比較多的關注。在北大醫藥已經因未及時披露政泉控股、北大資源控股簽訂股權代持協議事項受到證監會行政處罰的情況下,判決認為,該事項不具有重大性,主要理由是:該事項不屬于《證券法》第六十七條所列“可能對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重大事件”;股權代持雙方皆非北大醫藥控股股東,代持事項不影響北大醫藥的實際控制人地位;涉案事項并非虛增業績、隱瞞虧損等虛假陳述行為,對投資者決策無明顯的利好或者利空意義。
其實,類似判決,近幾年也時有出現。2016年,在證監會四川證監局已經做出行政處罰的情況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友利控股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2016)蘇民終732號”判決書中認為,針對友利控股未按規定披露關聯企業間交換及出售承兌匯票的行為,該交易行為本身并不導致公司主要財務指標失真,且2012年度報告對大部分交易亦有反映,案涉行政違法行為并未導致股票價格及成交量發生明顯變化;因此,案涉信息披露違法行為不屬于對重大事件在披露信息時發生重大遺漏。2013年,在華聞傳媒披露因財務會計報告重大會計差錯受到財政部行政處罰的情況下,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859號”裁定書從所涉金額、事件性質、影響力等方面進行綜合判斷,認為案涉財務會計報告中的有關事項和數據不構成重大事件。但是,目前北京、上海等絕大多數地方法院的立場與做法是,在受理民事賠償案件之前,虛假陳述行為所涉信息的重大性問題已經在前置程序中得到了認定,故在民事案件審理中可不予過多涉及而直接予以認定。
可以預見,這種民事認定與行政認定在實體上不一致的情形,還會不斷出現。隨著一些地方法院在立案登記制背景下開始突破前置程序限制,相關矛盾會變得愈發凸顯。1其中糾結,需要在深入研究虛假陳述行政違法責任與民事賠償責任構成要件、舉證責任銜接與區別的基礎上,加以厘清。與行政違法責任相比,虛假陳述民事賠償責任的認定顯然更為復雜。目前,證監會已著手推動司法機關修訂2003年起施行的《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2,建議從整體上把握以下方面。
一、進一步研究、細化虛假陳述民事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
上述《若干規定》在起草時,很大程度上參考了美國的學說理論與判例實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若干規定》實施兩年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做出了Dura案判決,把《證券交易法》10(b)條款下的民事賠償責任明確統一為六個要件:(1)重大不實陳述或者遺漏(a material misrepresentation or omission);(2)主觀過錯(scienter,包括故意、明知或者嚴重放任);(3)虛假陳述與買賣證券具有關聯性(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isrepresentation and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 security);(4)原告的交易系出于信賴被告陳述(reliance);(5)經濟損失(economic loss);(6)損失因果關系(loss causation),是指被告虛假陳述與原告損失之間存在“必然聯系”(causal relationship),或者說被告虛假陳述是原告損失的“實質性原因”(substantial cause)或者“近因”、“直接原因”(proximate cause)。3目前,美國聯邦法院體系基本遵照這六個要件處理虛假陳述民事賠償糾紛。對比分析可知,無論在司法解釋的條文規定上還是眾多已判決案件的實際操作上,我國法院對虛假陳述民事賠償責任構成要件的把握均比較初步、粗略。
二、區分“交易因果關系”與“損失因果關系”,合理分配舉證責任與確定證明路徑
上述六要件之四是原告的交易系出于信賴被告陳述,我國學理論述與實務上,參照美國學理的說法,往往也將此要件稱為“交易因果關系”(transaction causation)。由于證券交易不同于傳統的“面對面”交易,虛假陳述侵權不同于一般侵權,為解決原告在證明此要件上的困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88年Basic案中,以“欺詐市場理論”(fraud on the market theory)為基礎,確立了可反駁的“推定信賴”原則。該理論下,在一個有效市場,證券交易價格已經充分反映了所有公開、可得信息,包括虛假信息;因此,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當投資者以市場價格買入或者賣出證券,在其能證明以下情況時,推定其交易系出于“信賴”被告虛假陳述:(1)訴稱的虛假陳述是公開做出的,(2)該虛假陳述具有重大性,(3)股票在一個有效市場交易,(4)原告在相關期間實施了交易。42014年,聯邦最高法院進一步在Halliburton Co. v. Erica P. John Fund, Inc. Halliburton一案中維持了這一原則,不支持被告提出的原告應在證明存在“價格影響”的前提下才可適用這一推定;同時認為,如果被告有直接、顯著的證據證明其虛假陳述并未影響證券交易價格,或者證明涉案證券的交易市場并不 是一個有效市場,則可以推翻這種推定。5 上述六要件之 六是“損失因果關系”,美國法院要求證明此要件的路 徑是,虛假陳述的揭露導致證券交易價格下挫,原告應 當對此承擔舉證責任。
我國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規定》第十八條,也借助“欺詐市場理論”引入了“推定”原則。雖然對我國證券市場能否歸為“有效市場”、我國司法能否適用該理論一直存在爭議,實務上不少法院裁判已明確肯認我國虛假陳述賠償民事司法參照了這一理論。6但是,此種“推定”并未像美國那樣限于交易“信賴”或者說“交易因果關系”環節,而是籠統地將“交易因果關系”與“損失因果關系”一鍋燴地納入一個綜合性的“虛假陳述與損害結果存在因果關系”推定。7這種操作,部分地導致舉證責任分配的失衡。單從舉證責任上看,與美國相比,我國虛假陳述民事賠償原告的舉證負擔是相當輕的。一般情況下,原告只要符合虛假陳述實施日、揭露日與損失計算基準日等三個時點條件,列出交易與損失情況,就完成舉證了,不少分析證明工作留給法院承擔。這種模式,也部分地導致法院對證明路徑的認識扭曲。比如,關于交易“信賴”或者“交易因果關系”的推定與反駁,應基于虛假陳述后投資者買入或者賣出證券“當時”的情況,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鴻基地產虛假陳述案“(2016)最高法民申502號”裁定書中,以虛假陳述揭露后投資者還在買入證券,作為認定不存在交易因果關系的主要理由;這種“事后反推”的路徑是否妥當,頗值商榷。
三、處理好虛假陳述揭露日與證監會調查處罰的關系
虛假陳述的“揭露”(corrective disclosure),不僅對計算損失數額有意義,更是證明損失因果關系的要件性因素。由于證監會執法環節對虛假陳述行為采取“立案即披露,立案才披露”的做法,盡管這種做法不一定妥當,8我國司法實踐則普遍把被告公司公告證監會立案調查之日,作為確認虛假陳述揭露日的重要考量時點。筆者認為,在實際把握上,如果公告的立案調查通知書列明了調查事由為虛假陳述,則可以考慮把該日作為揭露日;如果公告的立案調查通知書只是模糊地說“涉嫌違反證券法規”,則虛假陳述并未被“首次”披露,因此尚不宜單純據此公告認為虛假陳述已經被“揭露”,還要綜合考慮公告前后的媒體報道(包括有影響力自媒體的報道)、股價反應、市場評論以及被告的自行糾正性披露或者監管部門最終認定的虛假陳述情況與投資者擔憂的一致性等因素。
近年來,美國聯邦巡回法院一系列不斷更新升級的判例,給我們提供一些雙向參考。2013年,第十一巡回法院在Meyer v. Greene案判決中指出,僅僅宣布受到美國證監會調查,“如果沒有其他情況,不足以構成揭露”;盡管隨著公司披露“受到美國證監會調查”,股價下跌,但是該調查并未確認公司此前披露的財務報告存在不實。9 2014年,第五巡回法院在Public Employees’Retirement System v. Amedisys, Inc.一案中認為,盡管關于政府調查的公告中并未披露存在實際欺詐,但是由于隨后的一系列部分性的披露揭示了欺詐情況,則披露政府調查與損失因果關系的認定相關;也即,盡管任何一個單一的披露不足以建立損失因果關系,但是一系列部分的披露綜合起來,就可以建立損失因果關系。10 2014年,第九巡回法院在Loos v. Immersion Corporation, et al一案中判決認為,僅是宣布啟動內部調查,并未向市場“揭示”(reveal)存在欺詐行為;啟動調查公布后的任何股價下跌,只能歸結于市場關于是否存在欺詐的猜測,這種猜測不能成為建立損失因果關系的基礎。11 2016年,第九巡回法院在Jacksonville v. CVB Financial Corporation一案判決認為,被告公布收到美國證監會調查傳票后股價大跌,綜合考慮此點與當時多位分析師認為傳票緣于被告虛假陳述、被告此后的披露確認了市場關于傳票的擔憂等情況,應當依據公告收到美國證監會傳票時確定損失因果關系。12
四、統一明確系統風險的認定與扣除標準
目前,在系統風險的認定與扣除問題上,各地、各案的做法差異很大。在被告上市公司住所地省會城市中級法院一審管轄的大原則下,地方保護的痕跡在系統風險扣除上若隱若現。有些判決認為被告提供的證據無法證明存在系統風險,不應剔除系統風險,被告要全額賠償;有些判決則認為投資者的損失100%是由系統風險導致的,不能得到任何賠償。有些判決以大盤指數作為考量是否存在系統風險的依據,有些判決以大盤指數加上板塊指數作為計算依據。具體如何剔除系統風險又有不同的做法,包括“統一確定系統風險直接比例法”、“統一確定系統風險相對比例法”、“個案計算系統風險直接比例法”等都有使用。在舉證方法上,一些地方法院希望證監會能像證券犯罪刑事訴訟中那樣出具“認定函”或者“確認意見”,也有些地方法院考慮通過專家證人、專業陪審員以及第三方鑒定機構解決這一問題。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在充分調研基礎上,加以統一明確。
五、區分信息披露違法與證券欺詐
目前,《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是一個“大筐”,既涵蓋了非常嚴重的財務舞弊、財務欺詐,也涵蓋了一般性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和重大遺漏,還涵蓋了“未按規定”也即未按照相關規則規定的時限、格式、內容、方式等披露。其實,許多信息披露違法行為,雖然違反了信息披露規則應當受到行政處罰,但并不一定存在“欺詐”,因此可能并不具備需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我國虛假陳述前置程序的存在,容易反向使投資者陷入凡是受到了證監會的行政處罰,就必然引發民事賠償責任的迷思。這一點,也是需要反思、梳理和澄清的。
六、區分發行文件與持續披露文件中的虛假陳述
我國《證券法》第六十九條是追究虛假陳述民事責任的基本法律依據。但是,該條未區分發行文件中的虛假陳述與持續披露文件中的虛假陳述,只是就不同主體規定了無過錯責任、過錯推定責任、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一級市場發行文件披露中的發行人與二級市場持續披露中的上市公司一樣,要承擔無過錯責任。筆者認為,二者在責任主體范圍、責任構成要件尤其是是否要求主觀過錯、舉證責任等方面應當有所區別。背后的邏輯是,在發行文件虛假陳述中,發行人本身就是因虛假陳述引致交易的一方當事人、直接受益者,發行文件中的虛假陳述,對投資者的侵害是明顯的;而持續披露虛假陳述中,上市公司并非投資者買賣證券的交易對方,也非直接獲益者,持續披露文件中的虛假陳述,對投資者的侵害是隱含的。
美國法下,證券民事賠償責任的立法與判例依據紛繁復雜、疊床架屋,多有交叉重合、以新代舊之處,原告也往往依據多個法條起訴。雖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指出的,共有8個“明示的”(express)證券賠償責任條款,即《證券法》第11、12、15條與《證券交易法》第9、16、18、20、20A,13但是,使用最廣、作用最大的反倒是聯邦法院體系基于“反證券欺詐一般條款”也即《證券交易法》第10(b)條及其下證監會10b-5規則,通過判例逐步推展出的“默示訴權”(implied private cause of action)。按照聯邦法院的解釋,《證券交易法》第10(b)條與10b-5規則創制了影響二級市場交易(aftermarket trading)的有意的(intentional)虛假誤導性陳述所應承擔的寬泛責任,原告既可以是買方也可以是賣方,索賠對象范圍較廣,舉證責任較重;而《證券法》第11條、第12條實質上創制了證券發行中發行人及相關主體的“嚴格責任”(strict liability),原告只能是買方,索賠對象范圍較窄,舉證責任較輕。《證券法》第11條與第12條的區別在于,前者適用于已注冊證券,任何買方,無論其從何人那里購入證券,均可要求對虛假誤導性注冊報告承擔責任者賠償損失,索賠對象是證券的“制造者”與“批發者”,包括發行人、承銷商以及幫助其準備注冊報告的“專家”;14 后者適用于所有證券,如果賣方在銷售證券時使用了虛假誤導性的招股書或者口頭陳述,買方可以要求撤銷買入,或者于不再持有該證券時要求賣方賠償損失,索賠對象是“零售者”也即把證券銷售給大眾投資者的交易商。15
在我國臺灣地區,發行文件不實陳述的民事責任規定于《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通稱“公開說明書不實責任”,而持續公開文件不實陳述的民事責任規定于《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項,通稱“財報不實責任”。16這種區別,也是我國將來在責任設定上需要重點研究考慮的。
進行以上分析后,回到本部分開頭提及的法院在涉案信息“重大性”上與證監會行政認定不一致的問題。通常來說,《證券法》以及證監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要求披露的信息,均是達到“重大性”程度的信息;證監會調查、處罰的信息披露違法行為,也是在認定涉案信息具備“重大性”要件的前提下,才實施執法行動的;個案中判斷“重大性”,應綜合考量“對投資者決策影響”主觀標準與“對交易價格影響”客觀標準。因此,司法判決認定已經受到證監會處罰的行為所涉信息不具有“重大性”并主要據此駁回投資者賠償請求,確有較大的令人糾結之處,相關裁判理由也顯得牽強蒼白。不過,如上所述,如果我們能進一步深化對虛假陳述民事賠償責任構成要件、舉證責任、行為樣態等方面的理解與認知,或許可以從交易因果關系、損失因果關系、主觀要件等更廣闊、更豐富的層面上找到更具說服力的解釋、解決途徑。
民事司法對證監會行政執法的反向推動
在當前各方形成合力、進行聯動防范與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的背景下,司法機關加強了對金融監管的介入,在某些方面還呈現出“司法監管化”的傾向。17一些法院系統人士在溝通中也認為,基于金融監管的局限性,應發揮司法“反身性”功能。長期以來,證監會行政執法一直在推動、配合證券欺詐民事賠償訴訟與證券糾紛商事審判。近期的一些案例,則呈現出兩種民事司法反向推動證監會行政執法的動向。一種動向是,“對于違反監管規定的行為,人民法院可以通過向金融監管機構發出司法建議的方式,由金融監管機構通過行政執法行為予以規范和整治”;18另一種動向是,司法機關開始顯露出以違反證監會監管規章為由認定商事合同無效的苗頭。這兩個方面均已出現典型案例。
一、地方法院向證監會發出《司法建議書》
2016年12月,江蘇安恰化工有限公司以上市公司輝豐股份的控股子公司科菲特拖欠其貨款為由,向常州市新北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常州市新北區人民法院“(2017)蘇0411民初113號”判決書顯示,經查明,輝豐股份審計袁仲和于2014年4月23日發給科菲特財務人員的電子郵件一份,載明2012年虛增銷售4781.6萬元。2017年10月,常州市新北區人民法院向中國證監會稽查總隊發出司法建議書》,稱“因江蘇輝豐生物農業股份有限公司并非本案當事人,但涉嫌通過合并財務會計報表虛增上市業績,擾亂證券市場秩序,損害廣大股民投資者的利益,故本院提供以上線索”。19 2018年1月,輝豐股份回復深交所問詢函稱,經核查,控股子公司科菲特2012年部分收入存在虛增銷售的可能,確認金額為3390.29萬元。2018年4月,輝豐股份公告,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被證監會立案調查。
從權限與程序上講,法院在民商事審判中發現證券違法情況,主動以司法建議書的方式提請證監會關注,并無障礙。但從以往實踐看,這種操作并不多見。隨著我國公眾公司卷入的合同、投資、知識產權等糾紛不斷增多,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上市公司在財務、經營或者管理等方面存在證券監管尚未關注到的虛假陳述的情況也會越來越多,證監會收到的司法建議書或許將不再是鳳毛麟角。這一動向,表面上是民事司法對證券執法的推動,深層次上也涉及法院在一些決定民事法律行為效力、民事法律責任承擔與分配的事實依據上,與證監會的認定是否一致,比如,是否都認定構成財務舞弊,從而既構成證券法上的欺詐,也構成民事合同締約或者履約上的欺詐。
二、最高人民法院認定股權代持協議無效
此即引起民商法學界與證券實務界高度關注、不無爭議的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3月做出的“(2017)最高法民申2454號”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20
本案核心爭點是,訟爭雙方在亞瑪頓發行上市前就其股權達成隱名代持協議有效無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認定,該種股權代持協議“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故而無效。其理由是:首先,依據證監會頒布的《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管理辦法》第十三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第三條,《證券法》第十二條、第六十三條規定,“公司上市發行人必須股權清晰,且股份不存在重大權屬糾紛,并公司上市需遵守如實披露的義務,披露的信息必須真實、準確、完整,這是證券行業監管的基本要求,也是證券行業的基本共識。由此可見,上市公司發行人必須真實,并不允許發行過程中隱匿真實股東,否則公司股票不得上市發行,通俗而言,即上市公司股權不得隱名代持。本案之中,在亞瑪頓公司上市前,林金坤代楊金國持有股份,以林金坤名義參與公司上市發行,實際隱瞞了真實股東或投資人身份,違反了發行人如實披露義務,為上述規定明令禁止”。其次,證監會根據《證券法》授權對證券行業進行監督管理,是為保護廣大非特定投資者的合法權益。“要求擬上市公司股權必須清晰,約束上市公司不得隱名代持股權,系對上市公司監管的基本要求,否則如上市公司真實股東都不清晰的話,其他對于上市公司系列信息披露要求、關聯交易審查、高管人員任職回避等等監管舉措必然落空,必然損害到廣大非特定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從而損害到資本市場基本交易秩序與基本交易安全,損害到金融安全與社會穩定,從而損害到社會公共利益”。“本案楊金國與林金坤簽訂的《委托投資協議書》與《協議書》,違反公司上市系列監管規定,而這些規定有些屬于法律明確應于遵循之規定,有些雖屬于部門規章性質,但因經法律授權且與法律并不沖突,并屬于證券行業監管基本要求與業內共識,并對廣大非特定投資人利益構成重要保障,對社會公共利益亦為必要保障所在,故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四項等規定,本案上述訴爭協議應認定為無效”。
可以說,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裁定意見,對證券行政執法的“反推”力則是巨大的。我國股票發行上市環節,出于種種原因,股權代持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我國臺灣地區將代持賬戶稱為“人頭賬戶”;更有一些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把“大非”偽裝成“小非”,以規避減持約束。對這些情況,監管雖有關注但鮮見作為違法違規予以查處的先例。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引發的問題是:其一,《證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規定的欺詐發行是“發行人不符合發行條件,以欺騙手段騙取發行核準”,最高人民法院裁定認為“不允許發行過程中隱匿真實股東,否則公司股票不得上市發行”,可見,發行人隱瞞此種隱名代持涉嫌欺詐發行;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將此種隱名代持行為的危害定性為“損害到廣大非特定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從而損害到資本市場基本交易秩序與基本交易安全,損害到金融安全與社會穩定,從而損害到社會公共利益”,則證監會理應對隱瞞此種代持情況的發行人、上市公司按信息披露違法予以查處,對代持雙方按照《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的“其他信息披露義務人”予以查處。
不過,迄今尚未發現證監會有所動作,也未看到證監會對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定性進行公開回應。或許證券監管上并不認為涉案股份代持的危害有多么嚴重,則最高人民法院以相當嚴厲的措辭從金融監管的角度認定合同無效,就有較大的商榷余地。此外,認定上市公司股份代持合同無效之后,還涉及名義股東如何退出、實質股東如何回歸正位的問題,需要證券監管的后續跟進;如果是控股股東所持股份的代持,還涉及上市公司收購事項,情形就更為復雜。
證監會行政執法對民事賠償的直接介入
《證券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和繳納罰款、罰金,其財產不足以同時支付時,先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就是證券執法上的“先民原則”。但是,實踐中由于行政、刑事處罰在先,相關罰款、罰金上交國庫,其后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勢必受到影響。21尤其是一些案件中,上市公司還可能因構成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態安全、生產安全和公眾健康安全等領域的重大違法行為受到其他行政部門的處罰或者刑事司法機關的追究,乃至被強制退市、被申請破產。22此時,如何協調各方面的利益沖突,使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最大限度地得到賠償,就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近年來,證監會在萬福生科、欣泰電氣案中首開保薦機構先行賠付,其下屬的投資者保護機構也積極支持投資者賠償訴訟,但這些終非普適治本之策。從長遠看,還是應當在立法層面與實際操作上,考慮借鑒參考美國證監會普遍使用的“公平基金”制度、英國金融行為局2017年首次使用的“直接勒令賠償”制度,以及香港證監會在洪良國際等案中使用的申請法院“責令回購”制度。
一、美國證監會的“公平基金”制度
公平基金的全稱是“聯邦投資者賠償賬戶”(T h e Federal Account for Investor Restitution)基金(FAIR Fund)。2002~2013年,美國證監會累計通過243只公平基金,補償投資者144.6億美元,超過此期間其120.4億美元的預算開支總額。23 2017財年,美國證監會沒收違法所得29億美元、民事罰款8.32億美元,通過公平基金補償投資者10.7億美元,其中絕大多數資金來自于四只公平基金。24美國證監會以公平基金制度為依托,同時使用接管(receiverships)、協同起訴(coordinated prosecutions),公眾公司財務報告發生重述時由公司收回已發放給高管的與運營表現掛鉤的紅利(clawback actions)等公權力干預手段,成為證券欺詐案件中與私人賠償訴訟并駕齊驅、互為補充的挽回投資者損失的主導力量。同時,有別于私人賠償訴訟主要針對實施虛假陳述的公眾公司,美國證監會收取公平基金的案件來源多種多樣,既包括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上的欺詐性披露,也包括發售未注冊證券、龐氏騙局與相關伎倆、內幕交易、操縱市場、投資公司與投資顧問的不當行為、經紀交易商違規、海外賄賂與腐敗等。另一個不同之處在于,私人賠償訴訟因種種限制,賠償金主要來源于發行人、上市公司,公平基金更有可能讓證券欺詐中的責任人員與作為次級被告的審計機構、投資銀行等幫助教唆者承擔經濟制裁;而且就責任人員來說,對于證監會的民事罰款必須自掏腰包,不能如私人賠償訴訟中可以利用董事高管責任保險(D&O)實際上把經濟處罰通過公司間接轉嫁給受損害的股東。
與美國期監會(CFTC)、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司法部(DOJ)相比,美國證監會擁有最廣泛的補償受害者經濟損失的授權。本來,美國證監會的預算體制是“收支兩條線”,預算由國會批準、財政支付,其執法收繳的罰沒款也悉數上交國庫。曾經很長一段時間,美國證監會也認為自己并不承擔補償投資者的職責,投資者賠償應通過私人訴訟渠道解決。25轉變發生于《1990年證券執法救濟與分值股票改革法案》(Securities Enforcement Remedies and Penny Stock Reform Act of 1990),明確授權證監會在行政程序中沒收違法所得并分配給受害投資者。不過,這項授權并不適用于民事罰款,證監會仍應將罰款交給財政部,所以當時設立的是“沒收基金”。1990~2002年間,證監會在兩類案件中使用該項授權:一類是個人通過欺詐獲得了可確認的違法所得,主要是內幕交易案;另一類是證券發行欺詐與龐氏騙局案中,違法機構除了欺詐外實際上別無其他商業目的,證監會通常尋求緊急救濟,關閉這些機構,任命接管人,把剩余資金返還給受騙投資者。
2001年與2002年接連爆出的多起重大會計舞弊丑聞給投資者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損害。2002年,《薩班斯法案》發布實施,擴張了證監會補償投資者的權力,第308(a)條授權證監會可以將民事罰款加入到“沒收基金”中,改稱“公平基金”。該條規定:“如果在證監會依據證券法發動的任何司法或者行政程序中,證監會獲得指令,要求沒收某人因違反證券法律或者其下的規則、條例所獲收益,或者該人同意和解上繳違法所得,同時證監會也依據相關法律對該人實施了民事罰款,則該項民事罰款應按照證監會的請求或者依照證監會的指示,為了該違法行為受害者的利益,加入到沒收基金中”。不過,這一修改的最大局限性在于,證監會只有在同時令被告上繳違法所得的前提下,才可將民事罰款一并納入公平基金。為此,證監會必須證明特定被告從證券違法中獲取了收益。如果只有民事罰款但無沒收違法所得,證監會就應將民事罰款悉數交給財政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2010年發布實施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取消了這一限制。該法案第929B條規定:“如果,在證監會依據證券法發動的任何司法或者行政程序中,證監會對違法者實施民事罰款,或者該違法者和解同意接受民事罰款,則該項民事罰款應依據證監會申請或者按照證監會指示,加入到為了該違法行為受害者利益設立的沒收基金或者其他基金中”。
美國證監會擁有是否設立公平基金的決策權。執法部職員在提請證監會發動訴訟或者同意和解時,會考慮是否建議設立公平基金。證監會主要依據兩種因素決定是否設立:其一,是否存在可確認的、蒙受了可確認損失的一眾受害投資者;其二,與潛在受害者數量相比較,可能從被告收取的罰沒款數量是否大至可以提供合理分配。實踐中,這兩類因素又被細分為三十個不同的可行性論證因素。
2007年,證監會在執法部成立了“收款與分配辦公室”(the Office of Collections and Distributions)管理基金分配。2011年,為加強分工制衡,將之一分為三:隸屬于執法部的“收款辦公室”(the Office of Collections)、“分配辦公室”(the Office of Distributions)與隸屬于財務管理辦公室(the Offic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的“執法審計與數據完整性處”(the Enforcement Audit and Data Integrity Branch)。具體操作上,在受害者及其損失都已明確、被告申請破產的可能性較小,而且被告值得信賴的少數案件中,證監會的處罰令或者法院的最終同意判決會要求被告直接將罰沒款支付給可確認的受害者。大多數案件中,證監會雇傭外部的分配顧問制定分配計劃,雇傭基金管理人發布通知、向適格參與者發送信息、實施追償、建立賬冊、進行納稅申報與分配資金。
虛假陳述案中,會出現私人賠償訴訟與證監會執法平行進行的情況。此時,證監會通常會同意把已經繳納的違法所得從私人集團訴訟的賠償款中扣除,但通常不同意將已經繳納的民事罰款用于扣減私人集團訴訟的賠償款,意在“維護民事罰款的威懾效果”。如果投資者已經通過公平基金獲得了足額補償,則法院基本上會駁回平行的私人賠償訴訟。同時,許多案件中,證監會把公平基金款項置入集團訴訟賠償賬戶,以避免重復與節約分配成本。
有些虛假陳述案中,證監會的執法對象是已經進入破產程序的公眾公司。根據絕對優先權原則,《破產法典》第510(B)條將股東因證券欺詐的索賠請求置于破產公司債權人的求償權之下。因此,針對破產公司的證券私人訴訟往往被駁回。但是,《破產法典》第510(B)條并未阻止證監會可以通過公平基金把罰沒款分配給受欺詐的股東,其實施結果是減損了破產公司無擔保債權人的利益,導致對股東的過度補償。典型例子是世界通訊公司案。世界通訊公司在揭露大規模財務欺詐后不久就申請破產保護,證監會從破產財產中收繳了7.5億美元作為民事罰款,設立公平基金分配給了本應顆粒無收的受欺詐股東。26此舉引起了相當多的學術和大眾批評。不過,世界通訊公司案僅是孤例。另外一起受到批評的北電網絡案中,公司向證監會支付3500萬美元民事罰款14個月后才申請破產,而且該筆罰款也未影響債權人的追討。27在其余的公眾公司已經進入破產程序的案件中,證監會或者不起訴公司,或者不對公司進行金錢處罰。此時,證監會往往注重起訴相關責任人員與審計機構、投資銀行等第三方被告,將所獲得罰沒款通過公平基金分配給受害股東,這并不影響無擔保債權人的利益。
總體看來,盡管公平基金制度也面臨與私人賠償訴訟重復、投資者自我循環賠償以及證監會行政和解中缺乏投資者參與等詬病,在聯邦最高法院繼續收緊虛假陳述案中私人集團訴訟可適用空間的趨勢下,作為公權力補償投資者的一種主要渠道,其未來發揮的作用會越來越大。28
二、英國金融行為局的“直接勒令賠償”制度
2017年3月,英國金融行為局首次使用《金融服務與市場法》第384條授予的勒令公眾公司賠償投資者損失的權力。特易購(Tesco plc、Tesco Stores Limited)因臨時公告高估半年度盈利,收到金融行為局的勒令賠償通知;Tesco承認指控,同意賠償購買其股票或者債券的適格投資者;金融行為局同意,如果賠償計劃執行滿意將不實施罰款。
《金融服務與市場法》第384條規定如下:“(2)在相關人符合以下情形:(a)實施了市場濫用行為…,且第(3)款條件成就時,[金融行為局]可以行使第(5)款規定的權力”。“(3)條件是–…(b)一人或者多人因上述市場濫用行為蒙受了損失或者受到其他不利影響”。“(5)本條第(2)款所指的權力是,要求相關人遵照監管機構行使權力、認為適當的安排,以上述損失或者其他不利影響為限,向適格的一人或者多人支付或者分配有關監管機構認為正當的數額”。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行為局的上述權力是強制性的,不容許討價還價。不過,為了促使違法者主動執行勒令賠償的決定,金融行為局把是否積極補償投資者,作為是否給予金錢處罰的考量因素。金融行為局《決定程序與處罰手冊》(Decision Procedures and Penalties manual,DEPP)第6.4.2(5)G)條規定,如果違法者已經承認違法并向監管當局提供了充分及時的合作,且已經采取措施保證那些因其違法行為蒙受損失的人會獲得足額補償,則可將此作為只給予公開譴責(public censure)而不施加金錢處罰的一種考量因素。不過,這還要取決于違法行為的性質與嚴重程度。
首例案件源自于2014年8月29日特易購公司發布臨時公告稱,截至8月23日,預計錄得大約11億英鎊半年度利潤;隨后,10月22日,公司又公告稱主要由于提前確認了商業收入和延遲應計費用,高估了半年度盈利數字。金融行為局認為,Tesco“知道或者應當合理預見到2014年8月29日的公告是虛假或者誤導的”,該錯誤公告導致其證券以被夸大的價格交易。Tesco plc、Tesco Stores Limited就其市場濫用行為與金融行為局達成和解,承認指控,同意向2014年8月29日至9月22日購買其股票或者債券的投資者進行賠償。此前,Tesco Stores Limited已經與刑事執法機構“嚴重欺詐辦公室”(Serious Fraud Office,SFO)達成“緩起訴協議”(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DPA),同意支付128,992,500英鎊罰金。29
金融行為局向Tesco plc、Tesco Stores Limited下發了內容詳盡、包含賠償協議格式文本的勒令賠償《處理決定書》(FINAL NOTICE)。決定書內容包括:1.處理決定 (ACTION);2.理由摘要(SUMMARY OF REASONS);3.概念釋義(DEFINITIONS);4.事實與相關事項(FACTS AND MATTERS),包括相關背景、發布不實信息的過程、不實信息對市場交易的不當影響、與SFO達成“緩起訴協議”的情況、配合金融行為局調查的情況等;5.失當之處(FAILINGS),釋明認定特易購行為構成市場濫用的依據;6.懲罰(SANCTION),指出特易購的行為違反了《金融服務與市場法》第118(7)條的規定,應當賠償投資者損失并受到公開譴責;7.程序問題,包括公開此決定的依據以及金融行為局“執法與市場監管部”的聯系方式與聯系人。決定書有兩個附件,附件1羅列了相關的法規與監管條文,附件2是“支付賠償金的具體安排”。該安排包括賠償金的管理人、潛在申請者的確認與通知、索賠程序、補償計劃、支付程序、計劃的終止、管理人的報告等內容,還包括兩個附錄。附錄1是投資者與Tesco plc、Tesco Stores Limited之間需要簽署的賠償協議格式文本(Release),包括當事人情況、簽約依據與背景、支付承諾與投資者放棄其他索賠的承諾、保證條款等內容。附錄2是涉案的掛牌交易債券情況。30賠償計劃由Tesco plc、Tesco Stores Limited委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作為管理人負責執行。
三、香港證監會的申請法院“責令回購”制度
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13條“強制令及其他命令”,賦權證監會就任何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及《公司條例》特定條文的行為,向原訟法庭申請強制令及其他命令。該條第(1)款規定:“在符合第(4)款的規定下,原訟法庭可應證監會的申請,作出第(2)款指明的一項或多于一項命令”。第(4)款的規定是:“原訟法庭在根據第(1)或(3A)款作出命令前,須在合理地可能的范圍內,信納作出該命令是可取的,并信納該命令不會不公平地損害任何人”。第(2)款指明的命令之一,就是:“(b)(如某人曾經(或看來是曾經)、正在或可能牽涉入第(1)(a)(i)至(v)款提述的任何事項,不論該人是否明知而牽涉入該等事項),飭令該人采取原訟法庭指示的步驟,包括使交易各方回復他們訂立交易之前的狀況的命令”。
2012年6月20日,原訟法庭應香港證監會申請,對招股章程中存在虛假誤導性陳述的洪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發出命令,責令洪良國際向之前在首次公開招股中認購洪良國際股份或在二級市場買入洪良國際股份,并在原訟法庭作出命令當日仍持有該等股份的7,700名投資者提出回購建議。這些股東可選擇是否通過回購計劃,以及是否接納回購建議。接納回購建議的限期于2012年10月29日屆滿,最后的接納水平為98.73%。這不但讓一眾股東可取回逾十億元的款項,而且向市場傳達明確的訊息,表明有一套機制可有效彌補因公司發出虛假或誤導性的招股章程所帶來的后果。31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參考借鑒美國、英國與香港地區的這些制度時,應充分考慮其在我國證券市場總體環境與法律框架下的可行性,避免出現證監會2015年推出的《行政和解試點實施辦法》、2014年《證券期貨違法違規行為舉報工作暫行規定》引入的舉報獎勵制度那樣,徒有條文規定但至今并無案例“破冰”,實際上處在“休眠”狀態。
結論與建議
如何在證券執法上維持行政、刑事與民事之間的“三角穩定”與“三角均衡”,是每個資本市場法域都繞不開的課題,也是一個充滿爭議與掣肘、博弈與往復的動態過程,需要基于本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狀況與證券監管、司法的現實框架,吸取成熟資本市場與其他新興市場的經驗教訓,不斷跟進和調整。
最近幾年,學理和實務上對證券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協調銜接關注、研究與探索較多,比如證券犯罪重刑化、輕刑化的導向與刑法的謙抑性,刑事移送標準的設定與調整,刑事證據與行政證據的相互轉化,證監會認定意見在刑事訴訟中的證據性質與效力,以及證監會與公安部門的平行調查等。對證券行政執法與民事司法協調銜接的關注,則基本局限于證監會鼓勵與支持投資者索賠,更具體言之,是支持中小投資者索賠。究其原因,既有相關問題凸顯度與監管敏感度的因素,更有深層次的理念導向因素。其實,無論從其他資本市場的做法還是我國資本市場的實際運行看,均需在保護投資者利益與維護公眾公司穩定持續經營之間尋求合理平衡與制衡。比如,是否認可證券執法與民事賠償領域的“二次傷害”與“循環賠償”,并從責任認定、責任配置等方面做出應對。32
本文旨在以所述三個問題為契機,引起立法、司法與監管對行政執法與民事司法協調銜接的重視,并找出適當可行的解決思路。在立法層面,建議正在提交審議的《證券法》(修訂稿)在虛假陳述責任條款上,區分、明確行政違法責任與民事賠償責任的適用范圍與構成要件,區分發行文件虛假陳述與持續披露文件虛假陳述,合理確定不同主體行政、民事責任的邊界與配置;并在已經列入的“先行賠付”之外,考慮引入“公平基金”、“直接勒令賠償”與“責令回購”等制度,利用公權力介入更為直接、高效、低成本的優點,使其與方興未艾的投資者民事訴訟索賠并駕齊驅,形成補償投資者的雙軌機制。在司法層面,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在修訂司法解釋與案例指導過程中,關注民事司法認定與證監會行政認定已經出現與可能出現的“不一致”情況,分析深層次原因,完善相關標準,在促進司法與行政協調的同時維護全國裁判尺度的統一。在監管層面,建議證監會持續關注民事司法裁判的最新動向,對一些模糊或者可能引起外界誤解的情況,及時研究、澄清,并就相關事項與司法機關保持有效溝通;同時,研究分析自身對一些已經或者可能引入的新制度、新機制的承接與實施能力。
證券行政執法與民事司法的協調銜接,還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問題。比如,行政證據轉化為刑事證據,已經有了新《刑事訴訟法》的依據,刑事證據轉化為行政證據,也有一些內部標準和程序;同時,實踐中,一些虛假陳述民事賠償訴訟的原告或者被告,也有借助行政執法證據的需求,但是證監會尚未開通相關渠道。行政執法證據轉化為民事訴訟證據,在我國其他領域已有實際操作。從域外資本市場的做法看,依據《澳大利亞證券與投資委員會法》第25(1)條規定,證券與投資委員會可以把監管執法中形成的詢問筆錄、獲取的會計賬簿與文件,制作成副本提供給適格當事人的律師;判例也明確,該規定的目的是“民事訴訟中得以使用證券與投資委員會強制檢查的成果”。這些操作與做法,也是值得考慮借鑒引入的。
注釋
1.比如南京中院受理的科林環保案、文峰股份案,成都中院受理的金亞科技案,杭州中院受理的祥云文化案。
2.2018年8月24日,證監會在江蘇南京召開證券投資者民事損害賠償救濟法律制度完善座談會,提出要進一步完善虛假陳述民事賠償等司法解釋。來自證監會官方網站。
3. Dura Pharmaceuticals, Inc. v. Broudo, 544 U.S. 336, 341-42 (2005)。
4. Basic Inc. v. Levinson, 485 U.S. 224 (1988)。
5. Halliburton Co. v. Erica P. John Fund, Inc., 134 S. Ct. 2398 (2014)。
6.比如,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魯北化工虛假陳述案“(2015)魯商終字第266號”等系列判決書中指出,我國虛假陳述賠償參照了欺詐市場理論的思路,以“推定”的原則,確定投資損失與虛假陳述之間的因果關系存在與否;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鴻基地產虛假陳述案“(2015)粵高法民二終字第1022號”等系列判決書中指出,只要《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第十八條設定的有關基礎事實存在,就可以推定因果關系存在。
7.參見鮑彩慧.證券虛假陳述民事賠償因果關系的規則再述[M].證券法苑,第二十三卷,法律出版社,2017,(12).
8.參見張子學.公眾公司應如何披露政府調查事項[M].證券法苑,第二十二卷,法律出版社2017, (02).
9. Meyer v. Greene, 710 F.3d 1189, 1201 n.13 (11th Cir. 2013)。
10.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of Mississippi v. Amedisys, Inc., 769 F.3d 313, 317-319 (5th Cir. 2014)。
11. Loos v. Immersion Corp., 762 F.3d 880 (9th Cir. 2014)。
12. Jacksonville Pension Fund v. CVB Financial Corporation, No. 13-56838 (9th Cir. Feb. 1, 2016)。
13. Musick, Peeler & Garrett v. Emp’rs Ins. of Wausau, 508 U.S. 286, 296 (1993)。
14. 第11條規定:“如果注冊報告的任何部分,在該部分生效時,包含關于一項重大事實的不實陳述,遺漏了一項使其中的陳述不致誤導所必需的重要事實,購買該證券者...可以起訴”。
15. Paul Vizcarrondo, Jr.,Bradley R. Wilson:LIABILITIES UNDER THE FEDERAL SECURITIES LAWS(2016),來自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律所官網。
16.參見賴英照.證券法律的未竟之業[J].中原財經法學,2012,(06).
17.“司法監管化”的說法較早見于最高人民法院前法官雷繼平2018年6月9日在北京大學金融法研究中心“資產管理業務監管:國際經驗與中國道路”理論研討會中的發言。
18.引自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長關麗2018年10月在“北京金融法治環境建設研討會”上的發言“強監管背景下的金融商事審判”,來自微信公眾號“法盞”。
19.參見張曉慶.法院向監管機構提交司法建議書科菲特業績虛增之問引出輝豐股份[N].每日經濟新聞,2018-02-04.
20.一個類似判例是“(2017)最高法民終529號”。該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信托持股協議》的內容明顯違反保監會制定的《保險公司股權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因而無效。該判決引起了巨大爭議。見“民商法沙龍”微信群討論實錄,金融監管行政規章與商事合同的效力---評福建偉杰公司、福州天策公司、君康人壽保險公司營業信托糾紛案,《商法界論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8年9月版;馬榮偉,金融監管與司法審查的邊界,《中國金融》2018年第20期。
21.參見張東昌.證券市場沒收違法所得與民事賠償責任的制度銜接[M].證券法苑,第二十三卷,法律出版社,2017,(12).
22.2018年10月,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吉林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長生生物違法違規生產狂犬病疫苗作出行政處罰,罰沒款合計91億元;同時,證監會擬決定對長生生物處以60萬元罰款的頂格處罰,擬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高俊芳等4名當事人給予警告,并分別處以30萬元的頂格處罰,同時采取終身市場禁入措施。此外,根據證監會2018年7月發布的《關于修改的決定》,長生生物將極可能被強制退市。
23. Velikonja, Urska, Public Compensation for Private Harm: Evidence from the SEC's Fair Fund Distributions (2015).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67, pp. 331-395 (2015)。
24. 見《美國證監會2017財年執法報告》,https://www.sec.gov/ files/enforcement-annual-report-2017.pdf。
25. Adam S. Zimmerman, Distributing Justice, 86 N.Y.U. L. REV. 500, 527 (2011)。
26. SEC v. WorldCom, Inc., 273 F. Supp. 2d 431, 435 (S.D.N.Y. 2003。
27. SEC v. Nortel Networks Corp., No. 07-CV-8851 (S.D.N.Y. Oct. 15, 2007)。
28. Velikonja, Urska, Public Compensation for Private Harm: Evidence from the SEC's Fair Fund Distributions (2015).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67, pp. 331-395 (2015)。
29.金融行為局案情通報,見https://www.fca.org.uk/news/pressreleases/tesco-pay-redress-market-abuse。
30.決定書全文見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finalnotices/tesco-2017.pdf。
31.來自香港證監會2012~2013年報,https://www.sfc.hk/web/annualreport2012-13/TC/assets/pdf/zh/06.07_enforcement.pdf。
32.在公司作為處罰與訴訟對象的情況下,直接與間接的不利后果事實上由全體股東共同承擔。如果原股東仍持有股份,則繼虛假陳述股價下跌所受傷害之后,再受一次傷害,是為“二次傷害”。如果不再持有股份,則等于新接手的股東賠償老股東遭受的 損失,是為“循環賠償”。